在本专栏《“仲裁地”的含义》一文中,笔者提到了“仲裁地”在国际仲裁中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到“仲裁地”(拉丁文Lex Arbitri,英文place or seat)与“开庭地”(英文 venue or place of arbitration)或“仲裁机构所在地”是不同的法律概念。
前文中,笔者曾提到有关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传统的观点是将仲裁条款视为“合同中的合同”,并可以根据“仲裁地”来确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进而确定其有效性 [1]。但最近几年,一些英美法国家的司法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司法实践是除非当事人有相反的约定,否则,合同的准据法应被推定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不过,无论是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的案例都显示,如果根据合同的准据法将导致仲裁条款无效,那么相关国家的法院仍有可能考虑将仲裁条款的准据法认定为仲裁地法律,以期达到“挽救”仲裁条款的结果,即将“鼓励仲裁”“让仲裁协议有效”作为优先考量的因素。当然这一原则也有例外。
上文的表述可能比较“绕”,难以理解。因此,笔者在此对“仲裁条款准据法”进行详细介绍,并介绍一个发生在英国和两个发生在新加坡的案例,希望能够将有关仲裁条款的准据法问题,包括英美法国家近期的司法实践阐述得更加清晰易懂。
首先,如 Redfern 和 Hunter 在其有关国际仲裁的重要著作中所言 [2],国际仲裁本身会涉及多个法律或规则体系,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
“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
仲裁庭的成立与仲裁程序进行所在地的法律(仲裁地法);
-
合同的准据法(纠纷解决所需要依据的实体法);
-
国际仲裁有关的规范、行为守则或指导性规范(比如IBA规范等“SOFT LAW”);
-
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有关的国际公约和执行地国的法律(《纽约公约》和执行裁决地的法律)。
在这五个方面的法律规范体系中,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第三项和第五项“合同的实体法”与“仲裁裁决执行地法”。一个是当事人选择的约束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法律,另一个是在裁决书作出之后,在仲裁裁决执行环节中需要考虑的执行地的法律。
上文提到的第四项,即非强制性行为规范、行为守则等,最著名的就是 IBA 规则,也称“软法”,属于行业自律规则或法律行业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指引,这部分内容通常不会引起企业或企业法务人员的关注。
最后,也就是第一项和第二项,即“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和仲裁地法对仲裁程序的规制,这是国际仲裁中的特殊问题,是诉讼程序中不会遇到的法律问题。
如笔者在《“仲裁地”的含义》一文中提到,如果是国内仲裁,不存在需要确定仲裁条款准据法的问题。比如国内的商务合同,默认的准据法是中国法;由于仲裁地也在国内,因此默认的判断仲裁条款效力所依据的准据法与合同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都是中国法,不存在冲突。
在国际仲裁中,由于双方当事人签约、履约,通常会涉及双方当事人所在国(如国际贸易合同,卖方将货物从货物所在地(通常就是卖方所在国)安排运输到买方所在地),因此合同权利与义务的履行,就会涉及买卖双方所在国两个不同国家的法律。为了避免麻烦,双方当事人通常会在国际贸易合同中约定该合同应适用的实体法,即二选一。这样,当合同的约定不足或不够清晰时,双方便可依赖他们共同选定的实体法。
合同双方在国际贸易合同中约定实体法时,一种选择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更常见的选择是买卖双方之一所在国家的法律。
然而,在谈判合同条款时,对于如何解决合同争议,各方最容易达成一致的仲裁条款,就是约定在当事人双方所在国之外的第三国进行仲裁。比如中方与法方之间的贸易合同,双方均可以接受到第三国进行仲裁(如新加坡),而不是一方必须到对方所在国(如中国或法国)进行仲裁。换句话说,双方会寻找一个中立的地点进行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也被称为“私人之间的诉讼”(private litigation),属于“准司法程序”。当仲裁在第三国(中立国)进行时,必须遵守仲裁地的仲裁法和程序法,而且仲裁程序也要受仲裁地法院的司法协助与司法监督,这就导致在国际仲裁中,必然会出现合同实体法与“仲裁地法”有所不同的问题。“仲裁地”成为确认“仲裁地法”的关键。
但是,第一项,即“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与第四项“仲裁地的法律规范”是不同的。前者单独涉及“双方当事人同意将合同争议提交仲裁”的这项“约定”作为一项“独立”于合同而存在的“约定”,是否合法有效等问题,属于仲裁程序能否合法开始进行的初始问题。“仲裁条款”是“单独存在”的“合同中的合同”。这涉及到底应当采用“合同约定的实体法”来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仲裁条款的解释、仲裁庭的管辖范围、甚至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还是根据仲裁地的法律来进行判断的问题。后者则涉及仲裁程序是否依法在仲裁地进行的问题。
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比如根据合同的实体法,得出仲裁条款无效,但根据仲裁地法律得出仲裁条款有效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如何确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就成为国际仲裁中一个特殊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呼吁企业或企业的法务人员(国际商事仲裁的潜在用户)关注国际仲裁的这个特殊问题,甚至建议在合同中除了写明合同适用的实体法,还应当写明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比如“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与合同约定的实体法相同”或“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即仲裁地的法律”等,从而避免出现一些企业难以理解的法律上的麻烦。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均在其示范性仲裁条款中加入了“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为XXX(比如中国香港法或新加坡法)”的建议,但相信绝大部分使用仲裁的企业或企业法务人员,未必真正理解这一条款的含义。
在国际商贸实践中,就仲裁条款的草拟问题咨询律师的情形非常少见;在仲裁条款里写明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的合同更是罕见。因此,希望在《“仲裁地”的含义》一文的基础上,本文能够对企业法务人员了解这一国际仲裁的特殊问题有所帮助。
01、传统的有关仲裁地与仲裁条款准据法的观点
简要地说,首先,纽约公约第5条(1)(a)项规定,要判断某仲裁裁决是否可以承认与执行,需判断其所依据的仲裁协议、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合法有效,或者仲裁地的法律、该仲裁条款是否合法有效。
实践中,通常判断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方式,就是根据当事人选择的“仲裁地”的法律进行判断。如,虽然合同约定的实体法是奥地利法,但仲裁地在瑞典,则瑞典法院认定瑞典法为该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并根据瑞典法来判断该仲裁条款是否合法有效[3]。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笔者《“仲裁地”的含义》一文的脚注中提到了英国上诉法院2012年的判例 Sulam é rica CIA Nacional de Seguros S.A. 诉 EnesaEngenharia S.A. 案(“Sulam é rica案”)[4]。为此,本文特增加对该案例以及两个新加坡相关案例的介绍,方便读者进一步了解有关仲裁条款准据法的法律发展。
02、2012年Sulam é rica案
英国上诉法院2012年的判例 Sulam é rica 案在国际仲裁界广受关注。
该案涉及一份在巴西修建的水利发电站的保险合同。由于发生了工程事故,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但保险公司认为该工程事故并不在保单承保范围内,而且投保人事前披露的某些信息不充分构成对保单条款的违反。
保单中约定的合同准据法是巴西法律,并且合同中对于争议解决约定有三个条款:
-
巴西法院对合同争议有排他性管辖权;
-
调解,即双方应当在争议提交仲裁之前,先将争议提交给双方选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如果90天内争议没有调解成功,任何一方可以要求终止调解程序;
-
仲裁,双方在合同中详细约定了在调解不成功时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并约定了仲裁员的产生、仲裁规定和仲裁庭的权限等细节,并写明仲裁地为伦敦。
在投保方提出索赔要求后,保险公司在英国伦敦启动了仲裁程序。
作为反制措施,巴西公司在巴西当地法院申请了“禁诉令”,禁止保险公司继续推进在伦敦的仲裁案。
同样,保险公司也在英国法院申请了“禁诉令”,禁止巴西投保人在巴西法院通过诉讼解决保险单项下的争议。
对于英国法院发出的“禁诉令”,巴西公司在英国法院上诉,主张:(1)“仲裁条款”应当适用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准据法,即巴西的法律;(2)根据巴西的法律,仲裁程序的启动必须得到投保人的同意,未经其同意而启动仲裁程序无效。
这起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是:究竟是适用合同约定的准据,即实体法巴西法律来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还是根据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地”伦敦的法律,即英国法来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
在这个案例中,英国上诉法院提出了有关判断“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的三阶审查法,即
-
当事人对于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是否作出明示的选择?
-
当事人如无明示选择,是否可根据证据推导出当事人的默示选择?
-
如无法推导出双方当事人的默示选择,则应当适用与“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有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法律。
在此案中,显然不存在当事人对仲裁条款准据法的明示选择。对于默示选择,英国上诉法院指出,合同的实体法通常可以被“默认”为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准据法的选择,即当事人选定的合同实体法对整份合同所建立起来的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仲裁条款构成约束。但是,在此案中,英国上诉法院认为,该保险合同的实体法对该仲裁条款并不构成约束。
首先,英国上诉法院注意到,既然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地是伦敦,则意味着仲裁程序会在伦敦进行,该仲裁程序将受到英国仲裁法的规范和英国法院的司法监督。英国上诉法院指出,这个结论与英国更早期的其他案例,包括C vs D XL Insurance Ltd vs. Owen Corning [5] 所建立的法律原则,是一致的。这两个案件所涉及的保险合同的准据法是纽约法,但仲裁地是伦敦,对此英国法院考虑到“仲裁地”的因素,认定英国法是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第二。英国上诉法院注意到,在此案中,如适用巴西的法律,则该仲裁协议必须、而且只能在投保人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执行,但合同中有条款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将合同争议在调解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提交仲裁解决。因此,如适用巴西的法律会导致一方“提起仲裁”的权利被“剥夺”,最终导致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结果。
英国上诉法院提出了三阶审查法,并指出在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示约定仲裁条款应适用的准据法的情况下,当事人提交的合同条款等证据不能推导出双方当事人默认的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就是巴西的法律,因为根据巴西法律,存在仲裁条款无法使用、仲裁程序无法被启动的风险,这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在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双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约定。
接下来,英国上诉法院找出根据,并做出与仲裁条款“有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法律”的判断。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尽管仲裁条款是合同的一部分,应当与合同有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但是,仲裁条款的目的不同于合同,是为了确保当仲裁成为解决争议的方式时,仲裁程序可以有法可依、合法进行,并得到必要的司法协助与监督,因此,当仲裁条款写明仲裁地为伦敦时,与仲裁条款有“最密切和最真实联系的法律”,就应当是仲裁地的法律,即英国法。
英国上诉法院指出,每个案件情况不同,因此对该问题的判断,应当在全面考虑案件的相关情形后做出。
总之,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英国法院在考虑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时,依据是“仲裁优先”原则,而不是“诉讼优先”原则。因为在这个案件中,共有三个争议解决条款,第一个是“巴西法院排他性管辖”,第三个才是“仲裁地在伦敦”并依据Aida Reinsurance and Insurance Arbitration Society (ARIAS)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本案显然是按照“仲裁优先”的原则,在仲裁条款与诉讼条款并存的情况下,英国法院并没有认可“巴西法院的排他性管辖权”。
第二,在该案中,法院是在对合同全文进行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包括是否存在相互矛盾的合同条款),而不是仅根据争议解决条款来做出判断的,这体现在法院注意到合同其他条款中有“双方当事人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仲裁”的约定。
第三,英国法院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合同约定的实体法应当与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一致(除非当事人有相反的约定),但当存在相反证据,而且出现依据合同的准据法会导致仲裁条款未必可以得到履行的风险时,应当出于“尊重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理念,同时考虑到仲裁程序应当依据仲裁地法律合法有序进行,因此,英国上诉法院得出了该案中的仲裁条款应依据仲裁地法(即英国法)的判断。
03、2016年新加坡BCY诉BCZ案
BCY诉BCZ是一起新加坡法院审理2016年已由法院裁决并发布的案件,争议涉及的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在合同草稿中约定合同的实体法是纽约法,但仲裁条款中约定新加坡为仲裁地。
在该案件中,股权转让协议虽经若干稿的修改并在最后得到了各方可以签署的认可,但在签署之前的最后关头,合同一方明确提出不愿意签署该协议,因此整份合同均未得到任何一方的签署。
随后,合同草稿的一方认为仲裁条款独立于股权转让协议而存在,依据仲裁条款向不愿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提起了仲裁。
不愿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则向新加坡法院提出异议,认为该仲裁程序中组建的仲裁庭对该项纠纷没有管辖权。
新加坡法院需要处理的争议焦点是:在各方均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该仲裁条款是否合法有效?要判断仲裁条款的合法性,就需要确定该仲裁条款到底应当依合同草稿中约定的纽约法来判断?还是依据仲裁地新加坡的法律来判断?
在这个案例中,新加坡法院认为Sulam é rica案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默示选择的仲裁协议准据法应当与其明示选择的合同实体法保持一致,除非有相反的情形。鉴于并不存在相反的情形,因此合同所适用的实体法就应当是表明“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的强有力标志”。新加坡法院因此确认纽约法应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而没有认定仲裁地新加坡法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 [6],使得“仲裁地”在确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方面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04、2019年新加坡BNA诉BNB案
在第二个新加坡法院案例的BNA诉BNB案中,涉案合同所约定的实体法是中国法。仲裁条款并未单独约定准据法,仅约定如果发生合同有关的争议,应按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
在案件中,涉及一方中国公司(甲公司)与韩国公司(乙公司)之间签署的工业气体的买卖合同。该合同的货物交货地在中国大陆。合同签署后,卖方甲和买方乙与另一家中国公司(丙公司)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韩国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被转让给了第三方丙公司,按照约定,该补充协议成为原有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后受让该合同权利与义务的丙公司作为买方没有支付货款,作为卖方的甲公司在新加坡启动了仲裁程序。案件中的被申请人要求仲裁庭就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理。仲裁庭多数认定仲裁庭有管辖权,于是提出异议的被申请人向新加坡法院提起了诉讼。
新加坡法院首先考虑了Sulam é rica案所确立的三阶审查法,并认为(1)各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合同的实体法为中国法;(2)仲裁地为中国,原因是上海并非一个单独的司法区域,而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因此当事人约定“仲裁在上海进行”,应当视为当事人针对仲裁地进行的约定(而不是将上海视为开庭地点)。
新加坡法院同意,在当事人未就仲裁地进行约定但约定了仲裁规则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其约定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规则的第18.1条规定,认定仲裁地点为新加坡。但是,在该案中,各方当事人已经约定了仲裁地为中国的上海,因此仲裁规则的第18.1条不适用。
对于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新加坡法院明确采用了Sulam é rica 一案确定的原则,认为在各方明示选择合同的准据法为中国法时,应推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也为中国法,虽然新加坡仲裁法规定的validation principle [7] 要求法院尽可能根据ut res magis 原则(即“解释合同条款的原则是尽量挽救合同条款的效力而不是相反”)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鉴于当事人已经明确选择了上海作为仲裁地,就算根据中国法律该仲裁条款很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条款(根据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国公司之间在国内履行的合同,其合同争议很可能不得通过外国仲裁机构解决)[8],其法律后果也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新加坡法院并没有要“不计代价”“挽救仲裁条款效力”的责任,否则在中国法院申请仲裁裁决的执行时,会给当事人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中国法被认定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并极有可能导致该仲裁条款无效,但新加坡法院并没有像Sulam é rica 一案那样,将仲裁地法(即新加坡法)认定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05、总结
对于非国际仲裁专业的人士而言,理解本文复杂的法律问题并不容易。笔者希望通过对案例的介绍和解读,可以使读者理解为何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示范仲裁条款中增加了一条“仲裁协议应当适用XX法律”条款的意义。
不仅如此,国际商事仲裁的用户也可以看到,国际仲裁因其“跨国界”的性质,涉及至少5个方面的法律体系,因此对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在涉及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的认定以及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不存在一个单一、简单的通用规则。
或许,通过这些案例,国际仲裁机构可以考虑向用户推荐这方面的“最佳实践”,即不再草拟和使用“仲裁条款”,而是使用单独草拟的《仲裁协议》作为合同的附件,改变现在将争议解决条款或仲裁条款放在合同正文中的做法。当准备这样一份《仲裁协议》作为合同附件时,希望当事人可以单独咨询国际仲裁律师的专业意见。
虽然实践中极其罕见,但无论是将《仲裁协议》作为附件,还是继续在合同中加入“仲裁条款”,笔者都认为,也许新的“最佳实践”,就是应当就“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向仲裁律师事前进行咨询,确保“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同时,根据合同的性质,在《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中标明“仲裁地”名称,并写明“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依据的准据法,以避免可能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因素。
*本文对任何提及“香港”的表述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脚注:
[1] 见 Redfern and Hunt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ixth Edition, Chapter 3. B.。
[2] 见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6th Edition, 2017。
[3] 参见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5th edition, chapter 3, B; 杨良宜教授《仲裁法-从1996年英国仲裁法到国际商事仲裁》第2章第8节,第115页。
[4] Case No: A3/2012/0249
Neutral Citation Number: [2012] EWCA Civ 638
[5] [2007] EWCA Civ 1282, [2008] 1 All ER (Comm) 1001.
14 [2001] All ER (Comm) 530.
[6] 参见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5th edition, chapter 3, B.。
[7] 及“应尽量将合同条款解释为有效而非无效的”原则。
[8] 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将涉外经济贸易纠纷提交至外国仲裁机构,参见《仲裁法》(2017年修正)第65条以及《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278条。虽然我国法律并未明文禁止国内当事人将无涉外因素的案件提交至境外仲裁机构,但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了对此类仲裁协议的否定态度。例如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2013)二中民特字第 10670 号)。
来源:金杜研究院,作者:叶渌,合伙人,争议解决部,ariel.ye@cn.kwm.com,业务领域:跨境商业纠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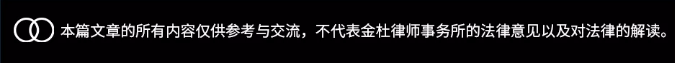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