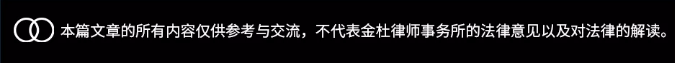01、《仲裁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于1994年8月31日颁布后 [1],虽有过两次修法,但《仲裁法》第16条到第20条,即有关“仲裁协议”(仲裁条款)的规定均未有任何变动。《仲裁法》该五个条款确定了仲裁法在仲裁条款方面的基本原则,其中第20条规定,如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仲裁机构或法院有权作出裁定。但一方请求仲裁机构、另一方请求法院作出裁定的,由法院最终裁决。也就是说,《仲裁法》确立了法院可以直接、不经过仲裁庭,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对仲裁条款的成立、解释、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和有效性等进行司法审查。
02、仲裁法修订稿中的变化
2021年7月30日,司法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下称“《2021年征求意见稿》”),其中与仲裁条款有关的立法建议与现有规定完全不同,可谓变化巨大、令人瞩目。
《2021年征求意见稿》第28条提出:对仲裁条款(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者仲裁庭的管辖权有异议的,应由仲裁庭决定。不仅如此,在仲裁庭组成前,须由仲裁机构根据表面证据决定仲裁程序是否继续;而且未经前款规定的前置程序就向法院提出异议的,法院不予受理。最后,该条还规定,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决定提出的异议,法院按照两审终审的程序进行司法审查,但法院的审查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2021年征求意见稿》的这一修法建议可谓是“颠覆性”的建议,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设置了前置程序,将法院从“一线”转入了“二线”,从可以直接受理针对仲裁条款有关的异议,变成了由仲裁庭优先对该问题进行裁定,只有在完成了前置程序后,当事人仍有异议的,法院才会对仲裁庭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03、曾经走过的路
1995年的《仲裁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第一部仲裁法。当时我国的仲裁机构少、通过仲裁处理商事纠纷的经验不足,《仲裁法》将有关仲裁条款内容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法院,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符合,无可厚非。
但是,多年的实践显示,对仲裁条款的司法审查,除了国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外,还包括涉外合同或国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一项技术难度颇高的法律问题。因为仲裁法不是法学教育的通识课,涉外合同或国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常常会涉及外国法,而且不同个案中当事人的约定不尽相同,因此仲裁条款的司法审查对法院而言,需要具备广泛的国际和国内仲裁法的知识,并非易事。目前,针对千变万化的情况,我国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以及对具体案件的一一批复,形成了“仲裁领域的判例法” [2] 和特殊的“报核制度”。
“报核制度”是法院内部针对仲裁条款效力的司法审查程序 [3],最初只针对涉外仲裁条款或国际仲裁条款的效力,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受理这类案件的“专属法院”。后来,无论是含涉外因素或非涉外因素的仲裁条款,如中级法院认为该条款无效、失效、内容不明或无法执行,需要做出“否定性”的决定时,须在做出该决定之前报请该院的上级法院即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审;如涉及含有涉外因素的仲裁条款,高级人民法院在认同中级法院的“否定性”结论前,须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是这类问题的终极裁判权威 [4]。
由于“报核制度”的实施,我国法院发布的与仲裁条款有关的案例数量较大。根据《中国商事仲裁年报-2016》报告:“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3278件,其中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34件、申请确认涉港澳台仲裁协议效力案件22件” [5];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12月23日首次发布的《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19年度)》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国法院旧存仲裁司法审查案件1649件,新收20528件,审结20513件,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高级法院报核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204件 [6]。虽然这些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但我国法院在确认仲裁条款效力方面的案件数量较大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对个案的批复和指示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就仲裁条款问题发布过多份司法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仲裁条款的内容所涉及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且对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指导 [7]。
04、瑕疵仲裁条款
打开“北大法宝”的搜索页面,输入“司法案例” “仲裁条款”,可以看到上万条信息涉及“仲裁条款”的案件信息,其中,不同年代的案例显示,仅仅是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案件就有相当数量,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的案件也大量出现 [8]。也就是说,有瑕疵的仲裁条款除了个案不同之外,同样的错误或瑕疵其实在不同年代的不同案件中均反复出现 [9]。(比如,租船合同与提单纠纷中涉及的“同款”的仲裁条款瑕疵尤其多见)[10]。
05、《2021年征求意见稿》第28条的优点和不足
《2021年征求意见稿》第28条的横空出世,即对仲裁条款内容的审查由仲裁庭决定的提议的出台,应当是体现了由法院对仲裁条款的内容直接进行司法审查这一做法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应当是司法界与社会相关各界已经认识到:在《仲裁法》实施20多年后,是时候将这方面的裁判权赋予仲裁庭了。
赋权给仲裁庭有什么优点?
首先,既然我国法律允许并鼓励商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而仲裁庭又有权对主合同的效力做出裁断,那么作为合同条款之一的仲裁条款(包括单独存在的仲裁协议)的内容审查,交给仲裁庭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仲裁属于当事人双方“私人之间的争议解决程序”,由当事人通过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授权”仲裁庭进行管辖,出现任何超授权范围甚至无当事人授权的情形,都会受到当事人的挑战并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监督。在这样的前提下,仲裁庭“滥用裁判权”的可能性不高,且可以通过司法监督得到纠正。
第三,仲裁条款的内容是否合法有效、是否清晰和可操作,单看仲裁条款的文字未必能够做出判断。当法院直接审查时,需要当事人提供案件事实与证据让法院充分了解案情。但是由于法院并非审理案件实体争议的机构,其投入的时间和累积的对案件的认识,在仲裁条款审核完毕之后就失去了意义。但如果仲裁庭负责对仲裁条款的内容进行裁断,该项工作就属于仲裁程序的一部分,仲裁庭花费在仲裁条款审查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将有助于加深仲裁庭对案件事实的了解。
第四,将这方面的裁判权让渡给仲裁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延误(如果当事人对于仲裁庭作出的决定不提出异议的话),而且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与国际接轨。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尽管全国仲裁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与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数量相比,仲裁案件的百分比仍然很低[11]。在司法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原本可以由当事人自行负担费用、让仲裁庭解决的商业争议,如果可以更多地分流到仲裁机构,可以大大节约对司法资源的占用。
当然,赋权给仲裁庭的优点很多,但也许有人会担心,如果让仲裁庭判断一个仲裁条款是否有效,仲裁庭会不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尽量确认仲裁条款有效?仲裁庭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不够“中立”“客观”?是否还是应当由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裁判?
笔者相信提出《2021年征求意见稿》第28条建议的专家一定已经意识到,由于司法监督权的存在,仲裁庭在做出这方面决定时,必须向当事人说明仲裁条款有效的法律依据以及有说服力的分析,就算当事人仍然不服,也可以将案件提交到法院进行司法审核。最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的众多司法解释与对个案的批复,这些累积了20多年的司法审判经验,足以给仲裁庭提供充分的业务指导,因此这种担心并无必要。
但是,《2021年征求意见稿》第28条的修法建议在笔者看来仍然是不足够的,因为仅将对仲裁条款(仲裁协议)的内容审查事项交予仲裁庭决定,仍然不能解决原本存在的问题:大量、频繁出现的瑕疵仲裁条款。比如,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或约定不明,会导致仲裁庭根本无法组成,仲裁程序也完全无法启动,因此,除非对《2021年征求意见稿》第28条做进一步的补充,否则该条款希望达到的目的仍然是无法实现的,而法院仍需继续承担由此带来的重负。
06、新的思路和建议
笔者认为,根据《2021年征求意见稿》第28条将审查仲裁条款内容的权力让渡给仲裁庭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必须解决不断重复出现的“瑕疵仲裁条款”所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裁判权其实是无法真正从法院转移到仲裁庭的。
根据我国法院多年仲裁司法审核的经验,参考国际仲裁中的做法,完全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来纠正仲裁条款中出现的“瑕疵”(即规定default position)。为此笔者建议在新的仲裁法中增加“仲裁优先”的原则,并且指定法院有权在符合“仲裁优先”原则的前提下,做出挽救仲裁条款的决定。
比如,新的仲裁法应当写明对于国内合同,凡当事人写明将合同争议提交仲裁(即有仲裁意愿)的,如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约定不明的,申请人所在地法院(比如中级人民法院)为法定的委任机构(appointing authority),有权在申请人提出请求时,替双方当事人从法院公布的仲裁机构名单中指定一家仲裁机构来受理案件,从而彻底解决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约定不明的问题;
比如,按照“仲裁优先”的原则,如果出现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仲裁条款,新仲裁法应当明确案件依法由仲裁机构受理;
再比如,如出现当事人约定两个仲裁机构的情形,同样按照“仲裁优先”的原则,如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申请人所在地法院有权指定其中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
总之,按照“仲裁优先”的原则,地方法院可以针对具体情况,以挽救仲裁条款为目的而做出适合于个案的决定,而不再需要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介入。
仲裁法规定实行“仲裁优先”原则,并赋予法院以挽救瑕疵仲裁条款的权力,可以永久性地克服“教育”大众所遇到的困难。通过立法挽救有瑕疵的仲裁条款,并不会否定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因为法院的决定是补充当事人之间“缺失”或“不明确”的约定,而没有“改变”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会违反当事人自治原则,也是符合国情的做法,可谓以“不变应万变”。
涉外合同或国际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能否采用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这也是可以探讨的。如果立法部门考虑在仲裁法中明确“主合同的准据法推定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除非当事人有相反的约定或根据主合同的准据法会导致仲裁条款无效”的原则,同时增加“如果依据主合同的准据法,仲裁条款无效的,则依据仲裁地法进行判断”的原则,这可以大大减少因为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而带来的麻烦。
让众多企业改变业务习惯,在合同中不仅要约定主合同的准据法,还要单独约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实在是比较“强人所难”。笔者虽然也赞同这一做法[12],但也认为不仅中国的企业做不到,国际上的绝大部分企业也都做不到。无论仲裁律师如何呼吁,国内外的当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在这一点上有大的改进。因此,与其要求企业在合同中区别两个不同准据法的效力并在合同中做出清楚约定,不如让他们记住要写明“仲裁地”更为容易、简便。
如此,如果主合同的准据法和仲裁地的准据法均认可仲裁条款的效力,两者没有冲突,当然就不会产生问题。但如果两者之间有冲突,比如按照主合同的准据法仲裁条款无效,但按照仲裁地法判断仲裁条款有效,当事人也无需为此争执,接受仲裁地法对仲裁条款的判断,即仲裁条款有效来通过仲裁解决争议。
总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以说国内的仲裁机构在管理上愈加完善并且积累了很多解决争议的经验。如果它们的受案量有所增加,仲裁的质量也可能随着机会的增加而进一步提高。但如果不提出挽救瑕疵仲裁条款的方法,无论是赋权给法院或仲裁庭,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各种原因会不断出现瑕疵仲裁条款的现实是很难改变的,就算新的仲裁法赋权给仲裁庭,对于仲裁庭作出的任何决定,当事人还是可以去法院提出挑战,这会导致有关仲裁条款的“战争”被进一步拖长,演变成“仲裁庭先审”,然后法院二审终审的局面。
结 语
当事人在仲裁条款内容方面的争执像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为了让商业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社会公共成本转为商界成本,减少对司法资源这一社会公共资源的占用,为了促进我国仲裁事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让我国200多个仲裁机构切实分担法院的受案压力,又由于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瑕疵仲裁条款的不断出现,因此,在本次仲裁法的修改中,除了确立赋予仲裁庭自裁权之外,笔者建议认真考虑增加“仲裁优先”原则,只要当事人表达了“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基本意愿”,就应当将案件提交仲裁解决。如果通过立法增加“法院有权挽救瑕疵仲裁条款”的原则,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仲裁庭面对“瑕疵仲裁条款”也无所适从的新窘境,让商业争议尽量进入“仲裁”的轨道,减轻法院负担,并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脚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于1994年8月3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第九次会议通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_人大网,并分别于2009年8月27日和2017年9月1日两次由全国人大进行了修法。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709/c8ca14070ead4c6d904610eea0f535fb.shtml 。
[2] 《中国仲裁二十年之制度回顾(3)——以1994年<仲裁法>为起点》,宋连斌,北大法宝。
[3]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1995年8月28日法发〔1995〕18号发布,根据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法释〔2008〕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调整);《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1998年4月23日的法〔1998〕40号文)以及《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1998年10月21日的法释〔1998〕28号文)。以上请参考北大法宝。
[4]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4》,第22-23页,北大法宝。
[5]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6)》第28-29页,北大法宝。
[6] 《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年度报告(2019年度)》,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8月23日,法释〔2006〕7号)第3—11、13条,北大法宝。
[8] 在北大法宝里面:司法解释-标题“仲裁条款”检索到94个案件,其中,仲裁机构没有约定共有28件,分别是第2、5、6、8、10、11、12、13、19、21、22、24、26、30、31、32、36、46、48、52、55、57、59、60、62、64、66条。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有14件,分别是第4、20、27、33、37、38、39、40、41、43、44、56、61、65条。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仅选择仲裁地点而对仲裁机构没有约定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1997年3月19日,法函〔1997〕3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戴维斯-标准公司与宁波协成电子电线有限公司买卖合同贷款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无效的请示的复函》(2004年6月25日,〔2004〕民四他字第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华太航业有限公司与安顺船务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仲裁条款效力请示的答复(2016年12月2日,〔2016〕最高法民他90号)。以上请参考北大法宝。
[10] 同脚注8。
[11]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14》(14页):比如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278.2万件,审结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5804件。也就是说,2014年,全国受理的商事仲裁案件约为全国审结的一审商事诉讼案件的4%,全国受理的涉外涉港澳台商事仲裁案件约为全国审结的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诉讼案件的31%。可见中国仲裁的发展空间很大,大有可为。请参考北大法宝。
[12] 参见笔者《第十一节:再谈“仲裁地”与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来源:金杜研究院
作者:叶渌,合伙人,争议解决部,ariel.ye@cn.kwm.com,业务领域:跨境商业纠纷
延伸阅读: